01
小说与悖论
我想先从我的阅读生活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。我似乎回想不起我是怎么学习识字和阅读的,好像生来就会了。阅读对我来说很自然,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就看见了文字。我的生活似乎从来是分成两种,一种是在实际当中度过的,就是吃饭、睡觉、和父母相处、和小朋友一起玩耍;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文字里,它给了我一个另外的空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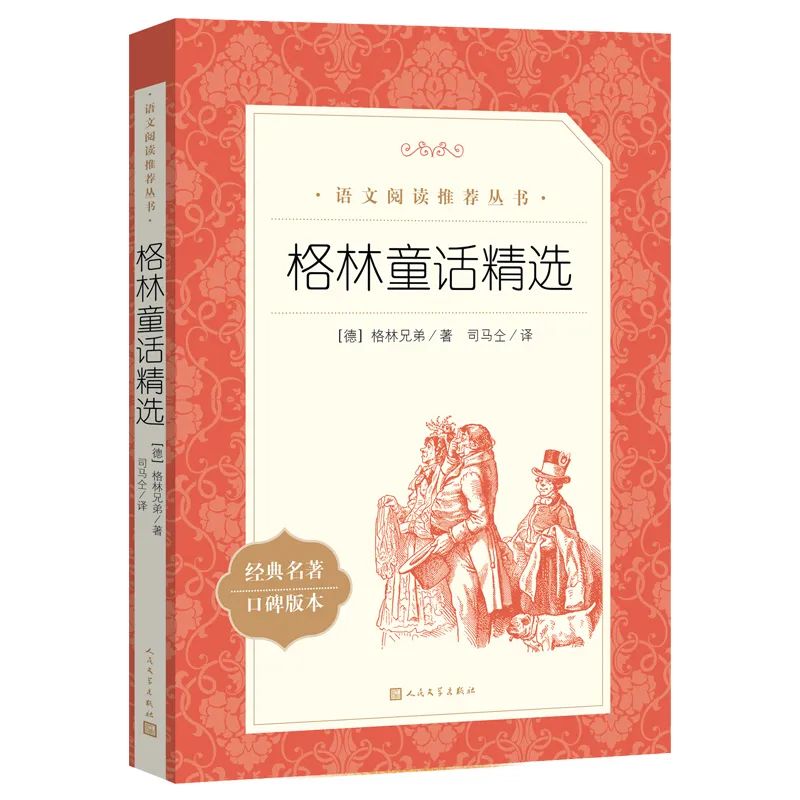
格林童话精选
[德]格林兄弟 著 司马仝 译
小时候,只觉得故事有趣,后来想起来,这有趣里藏着许多隐喻:为什么公主把懂不懂得害怕作为一个人智商的标准,害怕和智慧有关系吗?过度诠释一下,又似乎有关系。中国人不是讲求敬畏天地吗?再有,如果这***是有智慧的人,懂得害怕,那么他就不可能征服怪物,娶到公主。这么一来,故事不是没有了吗?所以,他又必须是一个***。这是一个悖论,小说往往都是悖论。
童话是很有意思的。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收集编撰过一部《意大利童话》,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。有一天,狐狸在树林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。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,兔子回说它娶了一个老婆。狐狸恭喜兔子,兔子说不要恭喜它,因为它的老婆很凶悍。狐狸说,那你真可怜。兔子说不,也不要同情它,因为老婆很有钱,带给他一栋很大的房子。狐狸再道恭喜,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,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。狐狸说可惜可惜,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,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。
我们写小说常常是这个样子。从起点开头,经过漫长的旅程走到终点,却发现是回到了原点,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过程,这原点就不是那原点。所以我们又很像神话里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,把石头推上去、落下来,再推上去、落下来……永远在重复做一个动作。但这一次和下一次不同,就是那句哲言:“人不会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。”
幼年时看童话故事,觉得很好看。它建设了一个奇异的世界,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。慢慢地,成年以后,我对童话的认识似乎递进着、常想常新,今天想是这个样子,明天想又有不同的感受。童话故事看似是孩子的阅读物,但其实,它的意味和形式,隐匿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里。阅读童话的经历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于
02
校园小说
再长大一点,开始上学,对童话的热情转移到接近现实生活的阅读。对于一个学龄孩子来说,最恰当的读物莫过于“校园小说”。“校园小说”的模式来自苏联,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写得很严肃、高尚,因少年儿童是未来的英雄,被赋予实现人类理想的重任。例如说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小说家盖达尔,他的小说《铁木儿和他的队伍》里的铁木儿成为少先队员的学习模范,很多学校成立“铁木儿小队”,一种浪漫的激情充盈在我们的学校生活里。铁木儿系列的小说里,有一篇名叫《雪堡司令》,我至今还能记得。
故事讲述街上有两队小孩,分属对立的两派力量,其中一派就是铁木儿。就像我刚才说小时候两条弄堂的小孩争斗打架,而小说将这种小孩子的罅隙政治化了,因而也变得严肃。铁木儿领导的一班小朋友很正义,不欺负弱者,做好人好事,而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,专门欺负小女孩。双方有一场战争,是争夺一座雪堡,即用积雪堆起来的堡垒,相持几日,胜负不决。有一天,铁木儿忽然带领队伍撤退,将雪堡让给“敌方”。原来,铁木儿从母亲口中得知,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牺牲了。故事很动人,孩子们拥有着美好的品德,高尚的情操,并且抱负远大。
其实这是一个先兆,预示着我逐渐分裂对文字世界的信赖。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世界的残酷,甚至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依靠。很快,生活就进一步地加剧分裂的状况。1966年,“文革”发生,我早早结束所谓“学业”,到了农村。我身边携带的书,除方才说的农村小说集,还有一本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,是当代中国作家浩然所著,写的是人民公社新农村的生活。小说里的农村景象光明开朗,前途美好,有阶级斗争,可是不像那个男孩的故事那么混淆阴沉,而是黑白敌我清晰,感情就不会受到严峻的拷问。有爱情,没有私欲,建立在公德和理想之上;有新旧观念的较量,总是进步的胜出。宣传画上拖拉机行驶在光芒四射的田野上的图景,在小说里演化成生动具体的人和事。
这和我所在的农村,在气氛上不大一样。我们村庄上,有一个富农的家庭,男人已经死了,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度日。这一家人都长得漂亮,高高的个子,五官端正。女孩子很苗条,她的外号也很妙,叫“铁嘴”。她很会说话,言辞犀利,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,几个来回就败下阵来。她不仅嘴厉害,干活也是一把好手。在我们那里,割麦子是用长柄镰刀,叫作“放大刀”。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过用大刀割草的场面,工具和姿势都类似“放大刀”,干活的都是男性壮劳力。可是,每每地,这个“铁嘴”女孩子都能进入“放大刀”的行列,她从来不落人后。
割麦的情景回想起来真有些戏剧化。我们的农民其实自有美学,割麦的季节里流行的装束:上身不穿衣服,光着膀子,肩上系一方白色的纱布,很彪悍也很俊美。在一列白披肩的队伍里,有一件花布衫,就是“铁嘴”。庄上人公认她是个人才,私下都为她惋惜,因为她的富农成分,一直没有寻到婆家。到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,她已经二十岁了。在农村,二十岁对于女孩,是个很可怕的年龄,很难有匹配的对象。她的弟弟也很秀美,同样娶不到媳妇。这一儿一女的婚事都是老大难。这是我在农村看到的阶级分野日常化地体现在个人命运上,和《艳阳天》里斗争的方式不同。书本里的世界固然美好,但却是简单的,它无法覆盖现实的复杂性,所以就变得脆弱。但阅读的经历,在我几乎成为信念,我并不因此而放弃,而是企图寻找出一个更有力量的文字里的世界。
我在农村里独自度过十七岁的生日。生日时,母亲送我一本小说叫《勇敢》,是苏联女作家薇拉·凯特琳斯卡雅所著,写的是上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发远东、建设共青城的故事,感情很激昂,合乎社会主义史诗的创作原则。母亲送我这本书是希望我振作,对目前的生活唤起一点热情,不要颓唐下去。当然她也知道书本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大的,可是除此,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?我们都是容易被书本激励的。
这本书如果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,就是“假”,但是小说确实写得很动人,这就是文字的能量吧!一群青年人在一片荒地上,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市是多么激动人心!乌托邦永远吸引着爱幻想的年轻人,但是成长会告诉我们,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在于它的不合理和不人道。前面说过,那个少年英雄出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,本来是个不幸的孩子,却被塑造成英雄。而《勇敢》所写的开发远东,正是在中国黑龙江边境,带有扩张的意图,结果也是失败的。在不断阅读和学习中,你会发现,在你非常投入、寄予很高理想的那个世界也是有谎言的。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,警告我们,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,还有诗。诗和真并列,当我们离开真实的时候,也许也与诗背道而驰了。
所以在写小说时,你要清楚你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字世界。我庆幸我一生总能得到一些启迪,总有人或事引领我,让我走到相对正确的道路,不让我失足。大量混杂的阅读中,你其实很容易走上歧途;但另一方面,所有这些,不论错的和对的,具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,纳入你经验的生活中,潜移默化,建立起明辨是非的可能性。生活中的缺陷使我情愿与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,远一点,书本就提供了这个机会。它们和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相似,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联系。
总的来说,我就是特别需要一个和我实际度过的世界不一样的空间。我不是要藏身逃避其中,而是它让我对我现实的遭遇有抵抗力。当然,它也许加剧我更不喜欢现实生活。要等到书本能帮助我度过这个分裂的时期,令我对正在经验的世界有一点喜欢,还需要很长的道路,还要经历更多生活,读更多的书。因为事实上,写小说的人如果不喜欢生活的话,是无法写小说的。小说和诗不一样,小说跟生活很接近,它是世俗的性格,是人间的天上。
03
爱情小说
让我再谈一下年轻时读的书。我常说我很喜欢托尔斯泰和雨果,但年轻时托尔斯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,也不特别喜欢雨果。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,这个名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,因为俄国文学不是今天的时尚。在我年轻时,我其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小说。小说里俄国的政治背景,知识分子的苦闷,思想没有出路,那些更深刻的内容我不怎么了解,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模糊的。读书就是这样,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,不喜欢的、看不懂的东西就放到一边,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识,好像反刍似的。于是,我就只看到爱情的部分。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总是有爱情,而且是不幸的爱情,年轻人多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爱情,而是受爱情的悲剧吸引,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。
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不是白读的。慢慢地,我们就建立起一种道德美学,那些深情的爱人们,并没有放弃利他心。虽然爱情是自私的,但是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着他们,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高尚理解,悲剧就是在这里发生。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阅读时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,他笔下的人和事,于我的处境称得上奢侈,但为什么我能够从中得到慰藉和启发?可能是有一个秘密通道,可能是青春,可能是对爱情的向往,也可能是成长的需要。
这大约可说是阅读生活的真谛,你和某一本书——不知是哪一本,会有一个秘密通道,就是这个秘密通道,令你在书中遇到知己,能和这本书邂逅,就是幸运。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共十卷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也是一部很好看的长篇小说。傅雷先生译的中文版,分成四本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第一本,里面包括前三卷。这前三卷,恰是人物从幼年到少年走向青年的成长过程,每一阶段都有一段爱情。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读者来说,非常令人激动满足。
弥娜生活很简单,又没到进入社交圈的年龄,成天无事可做,难免胡思乱想。克利斯朵夫的这一吻,给了她新发现,原来她已经被这个男孩深深地爱上了。爱情遮住她的眼睛,再看克利斯朵夫,他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变得可爱,钢琴弹得好,才华横溢,他的粗鲁只不过是男子气概的表现,他的破衣烂衫则是艺术家的风格,连他长相都变得英俊起来。克利斯朵夫呢,也以为自己其实早已经爱着弥娜,彼此的敌意不过是爱人之间常有的小别扭。于是,双双陷入情网。这一段爱情很快就被弥娜的母亲看在眼里。她是一个雍容大度的女性,她赏识克利斯朵夫的才华,但也明白他所属的阶层和她们不同,他和女儿之间只是孩子的游戏,一个不恰当的游戏。所以,就不要继续发展,而是及时收场,她带着弥娜离开了。
之后,克利斯朵夫遇到萨皮纳,展开了第二段爱情。年轻人对爱情的想象是概念化的,所以萨皮纳的故事让我有一点不满意。第一,她比他年长,是结过一次婚带个孩子的小寡妇;第二,她出身不怎样,既不是公主,也不是灰姑娘,而是个老板娘,开一间针头线脑的小店,显然缺乏女主角的浪漫色彩。还好,他们爱情的发生比较有戏剧性。他跟着萨皮纳去乡村参加亲戚的婚宴,郊游和歌舞制造了一个民间的欢场,暗中萌生的情愫迅速滋长起来。
因为大雨留宿小旅馆,他们隔着薄薄的墙,一举手把门推开就打破通道。两个人都知道墙那边站着对方,等待对方下手,可是都没有足够的勇气,最终蹉跎了时机。这个结局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悲剧想象,而当过后再读小说,方才理解,要使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,需要经过许多磨炼,和弥娜只是练手,仿佛过家家式地模仿成人关系;到了萨皮纳却是情欲露出水面,这不仅意味外部的生活在进展,更是内部——即身心发育成熟。
第三段爱情更加使我不高兴了。阿达是个粗鄙的女性,在一间帽子店里做店员,这个就更世俗了。她和克利斯朵夫并没有经过任何精神上的交流。和弥娜有钢琴课,萨皮纳有船上的合唱,阿达虽然也是邂逅于郊游,同样进了乡村小旅馆,但却是刻意安排,目的明确,迅速地上了床。这对于我们的道德美学、禁欲教育,最重要的是,罗曼蒂克的爱情憧憬,都太庸俗、太暴露。最令人失望的是,克利斯朵夫对此非常满足。那时候,我们只有第一本,之后的三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拿到。多年以后,阅读全书,原来还有安多纳德和葛拉齐亚在等着我们。这时候,我们的阅历和阅读,已经积累到可以更尽情地享受其中悲怆的诗意了。就仿佛,和书中人物克利斯朵夫共同成长起来。
这些章节在年轻时候被视作累赘,草草掠过,现在却觉得精彩极了!非常感谢傅雷先生,他翻译得那么好,真是一场文字的盛宴。据法国文学的专家说:“傅雷先生可说重写了这本书。在法国文学中,罗曼·罗兰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,这应该归功于傅雷先生的再创作。”有时候,一本书,在你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营养,成为人生经验之一种。
《简· 爱》也是那时我喜欢读的一本书。我读《简·爱》是在“文革”的黯淡日子里,那故事远离现实,遥不可及,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,幸和不幸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。当我读过许多书以后,再看《简·爱》,难免觉得简单了。爱和自尊,经过跌宕起伏的波折,最终保持圆满的结局,过于甜美,近似类型小说。但是,正因为此,它滋养了我枯乏的生活,缓解了我的苦闷。
阅读令我的生活变成两个世界——实际度过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,两者的关系我很难解释。它们好像是并行的,甚至互相抵触,但它们似乎又是有交集与和谐的。我站在书本里看实际的生活,同时,又在实际的生活里观看书本里的。它们之间相隔着距离,这距离开拓了我的视野。
(本文选自《小说六讲》,作者:王安忆,原题为《文字里的生活》,转载自微信公众号:凤凰网读书)


















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
共0条评论